播客文字稿|社交媒体和AI让我们更孤独了吗?(ep.50)
勇敢地去冒险吧,哪怕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冒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社交媒体”这个名字其实有点奇怪。或者说,社交媒体确实一开始是想让所有人都连接起来,让社交变得更容易。但是,很多人现在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沉迷于社交媒体之中,天天和我们互动的是手机,反而,面对面的、和真人的社交少了很多。而社交媒体的世界里面,你要说真的有让人很满足、很受益的社交吗?那可能也是少数情况。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交媒体反而让社交变得更稀缺了。
本期播客,我们聊的就是和“社交媒体年代的社交”有关的话题,而且我们的话题还扩展到了“AI年代的社交”。我请到的嘉宾是我的博士学妹、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的裴瑞,我们一般叫她裴裴。裴裴的研究兴趣正是人们的社交行为,而且尤其关注社交媒体、AI等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交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聊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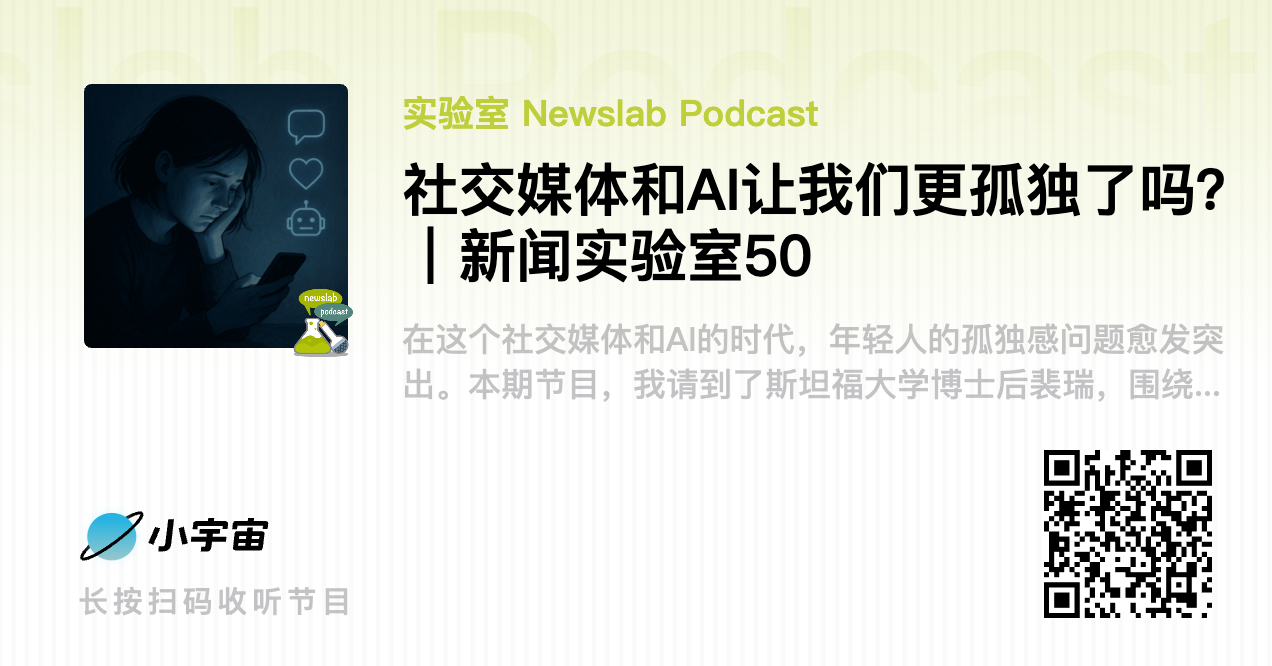
收听链接:小宇宙|Spotify|苹果Podcast
RSS地址:https://feed.xyzfm.space/xxkgbvrglujv
社交冒险:拒绝喝酒、尝试表白
方可成:欢迎大家来收听本期的新闻实验室播客。非常开心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她也是我在博士阶段的学妹——裴裴,你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裴瑞:大家好,我和可成学长是在宾大读博的时候认识的。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的本科是在布朗大学,读的是认知神经科学。大四的时候,我想做的工作是通过研究去回答一些问题,所以申请了很多PhD项目,也申请了一些咨询公司的工作。最后被宾大传播系的博士项目录取了,就去了宾大Annenberg传播学院。
方可成:有没有遗憾?没去咨询公司?
裴瑞:没有遗憾,哈哈。不过有一点遗憾是没有休息一下。我很幸运,一路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当时去了其他实验室的话,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路了。幸好被自己很喜欢的实验室接受了。
方可成:裴裴当时在宾大的实验室,在我看来是我们整个学院里面最Facny的,科学方面前沿的,最让我们搞不懂的,因为它是分析人脑的,对吧?
裴瑞:我们的实验室叫神经传播实验室,是用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传播学的问题。当时在学院里大家都叫我们"brain people"——大脑人。
方可成:比如说,人看了某条新闻之后,脑子里面某个区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粗浅的理解是这样。
裴瑞:对,或者是通过广告说服别人的时候,到底是大脑哪个神经回路发生了变化。
方可成:裴裴比我晚毕业,所以之后的经历我也不是非常详细了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博士毕业之后的经历。
裴瑞:我在读博时做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青少年的健康传播,就是怎样帮助青少年预防吸烟、抽大麻、喝酒等行为。做的时候发现,一是很难,二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这些青少年自己想要尝试,比如突然想喝酒尝尝是什么味道。往往是在社交情景下,别人让他喝酒,然后他在社交压力下选择了喝酒这种健康上有风险的事情,是为了避免社交上面的风险——如果拒绝的话,别人会觉得我不合群或者不酷。
方可成:别说青少年了,在中国各种年龄层都受到社交压力要喝酒吧?
裴瑞:哈哈,真的是。我后来也做了跨文化的研究。后来想,如果要研究这个问题的话,根源其实是社交冒险,所以我就到了斯坦福大学心理系Jamil Zaki的实验组,专门做社交冒险这个课题。
方可成:社交冒险是你当时进去之前就已经知道的概念吗?它是已经很成熟的概念体系了吗?
裴瑞:不是,这个是我提出来的。
方可成:你提出来的?哇,你好厉害,你已经有一个自己的理论了。
裴瑞:真的太难了。提出这个之后我导师很感兴趣,之前的导师也很感兴趣。但很难的是,你把它提出来之后,所有时候都要先跟人解释一遍什么是社交冒险。所以我很期待有一天我能直接说"社交冒险",然后别人就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方可成:那你就是绝对的大佬了。所以你刚才那个例子里面,我的理解是社交冒险就是你敢于在群体压力之下说“我不喝酒,我不抽烟”,是吗?
裴瑞:它是社交冒险其中的一个部分。社交冒险简单来讲就是社交中不确定性的、可能有不确定社交后果的行为。比如说表白,也是一个大家可能很快能理解的例子——你不确定对方会怎么样回应,对你来说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它也可以很小,比如我去邀请一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喝咖啡,或者我来做一个播客,也是有很多社交方面的后果,正面的、负面的可能都有。
年轻人越来越孤独
方可成:明白。那你带着自己的概念到斯坦福做博后,但做博后期间还是要参与导师的项目,对吧?总体来说你们在斯坦福的实验室是做什么呢?
裴瑞:我们在斯坦福做的研究叫斯坦福社群研究。它在我来之前就开始了,是2018年左右开始长期追踪本科生,看他的社交生活的不同方面怎样影响这些学生的身体健康。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项目,现在一直在进行。
方可成:很适合你的概念发展。
裴瑞:对,很适合。而且它的数据有很多样:不仅仅有问卷的追踪,还有社交网络——因为我们和学校直接合作,可以大规模地问这些学生“你是谁的朋友”,通过这个来画出他们的社交网络;里头也有神经科学的数据。还有一些是每年有三周,我们会更加密集地追踪这些学生的生活,从早到晚在每天不同的时段给他们手机上发一个很简短的小问卷,他们当下就必须完成。问你现在在哪?你在和谁说话?你心情怎么样?这种不同方面的追踪,加上纵向的长期数据能够帮我们理解很多可能以前只有横向数据时无法理解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证据。
方可成:那会不会长期到毕业之后还在追踪呢?
裴瑞:对。今年我们第一次要加入毕业之后的部分,看学生毕业了之后还和谁在保持联系,或者他们工作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快乐这一类的问题。
方可成:所以这个叫community project,它其实是一个社群、群体的概念,社交是在community的核心,是吗?
裴瑞:对,我们很关心从个体来讲的大家的心理健康状况,但从群体来讲就是斯坦福本科生作为一个整个群体的健康状况。这个项目里也有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说你附近的人,虽然你可能都不认识他们是谁,这些人的状态——不管是他们的情绪状态,或者是他们对于别人情绪的影响和感知——都能够间接地对你自己产生影响。我觉得作为社群概念这方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方可成:这挺有意思的。那在斯坦福的学生群体中间去研究他们的状况、社交、朋友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最近跟大陆、香港、台湾的一些老师交流,发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有很普遍的困惑——在大学里面当老师,这个年头大家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很难和学生之间建立连接。在课上很多同学,大部分同学都会说自己是i人。
但我在想,i人难道不应该是50%吗?怎么会大部分人都说是i人,甚至是90%的人都说自己是社恐?这好像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我还听说过一个非常有点离谱但也很有意思的案例,台湾的一个老师跟我说,她今年带了一些研究生,学期开始的时候先请大家一起吃个饭。在吃饭之前有一个学生给这个老师发邮件说,在吃饭的时候,请老师目光不要在我身上停留超过10秒钟,否则我会非常不适应。那个老师就觉得很无奈,回复说好我一定会尽力做到,但问题是我都不知道你是谁,我都不知道哪个是你,如果到时候我不小心在你身上停留了超过10秒钟,请你原谅。
所以这样的案例好像是很共通的,就让我们觉得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我们出了问题吗?是学校出了问题吗?还是说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提出来一些假设,觉得有可能是因为Covid——比如这些人是在Covid期间去读中学的,本来应该是青少年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社交的时期,他们没有这个机会,都被关在家里面。或者我们觉得可能跟社交媒体有关,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展开来聊。所以我很好奇这种情况在美国会有吗?还是说这是东亚文化里面比较多的情况?
本内容需加入付费会员后查看
Unlock full access to 新闻实验室Newsletter and see the entire library of members-only content.
订阅已经有账户? 登陆


